
如若回溯綿延數千年的中華文化,古籍,是繞不開的題眼。紙頁里的文明履痕仍在,典籍中弦歌不絕,山河萬古,文脈存而至千秋。
據估算,我國現存古籍約有20萬種以上,數量超過5000萬冊件。修復現存損壞的全部古籍,需要300余年。
2018年5月9日,天津師范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揭牌,成為我國北方第一家古籍保護研究院,正如名稱所指,它培養的,是致力于專業從事古籍保護的年輕人。青年與古籍,構成這個故事的全貌,他們從時間的兩端出發,涉渡千載,在此相遇。
被文明的燭火長久地照徹過后,一個個微小卻持續的變化由此產生,如種子播撒。
事經久,人年少
新學期伊始,天津師范大學,在一堂面向全校本科生的通選課上,話劇《趙城金藏》正在上演。
劇中故事發生在20世紀40年代。駐扎在山西趙城廣勝寺附近的侵華日軍,虎視眈眈地覬覦著廣勝寺內的《趙城金藏》。八路軍戰士和游擊隊員經過4個多小時搶運,將5000卷藏經全部轉移,運抵安全地帶。此后,稀世珍瑰《趙城金藏》被安全地保藏和修復,與《永樂大典》《四庫全書》《敦煌遺書》并稱為國家圖書館“四大鎮館之寶”。
劇本是授課教師周余姣依據史實原創的,課堂上近50個學生,她特意設計了20多個角色,意在讓大半個班級都能加入。一節課有3個課時,最后45分鐘專門留給學生們排演。有的學生特別“能放開”,會主動加入動作設計;有的很興奮,聽說要“玩”,“眼睛都亮了”。

天津師范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青年教師周余姣
大家的專業各不相同,外語、教育、廣告、計算機……周余姣知道,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會從事古籍保護,“但我希望學生心里有這個念頭,希望他們知道,古籍保護事業的存在”。
周余姣的課堂總與別人不同,她像是做負重拉練——三個大包,十多斤重,各類雕版、裝具、拓本、線裝書,塞得滿滿當當。“總想著多展示一點,沒準兒學生會感興趣。”她還隨身帶著小零食,作為學生認真聽講的獎勵。
有非古籍專業的學生問她,自己做了有關宋版書的畢業設計,可不可以請她來帶。還有學生課余寫了題跋研究的論文,拿給周余姣看。
“蠻好”,周余姣說道,“說不定,這些學生考研會報考古籍方向呢。”
古籍保護,對本科生來說也許是“念頭”,對碩士研究生而言,一旦選定該研究方向,意味著一只腳已經踏入這份事業。教師胡艷杰想知道,學生們如何看待自己的選擇。
2023新學年第一堂古籍原生性保護課,她給研一新生們布置了一份特殊的作業:介紹自己,并講述為什么報考。
在收上來的20多份手寫紙中,有人因為看了古籍相關的紀錄片從而產生興趣,有人是在文博展覽中被一套宋刻孤本吸引,從而喜歡上古籍。
其中一份回答令胡艷杰動容。這個女孩是“三跨生”(即跨地區、跨學校、跨學科考取的碩士研究生),本科專業是父母選的,她并不喜歡。作業末尾寫著:“直到來這里,學了我喜歡的古籍方向,我才真正有了上大學的感覺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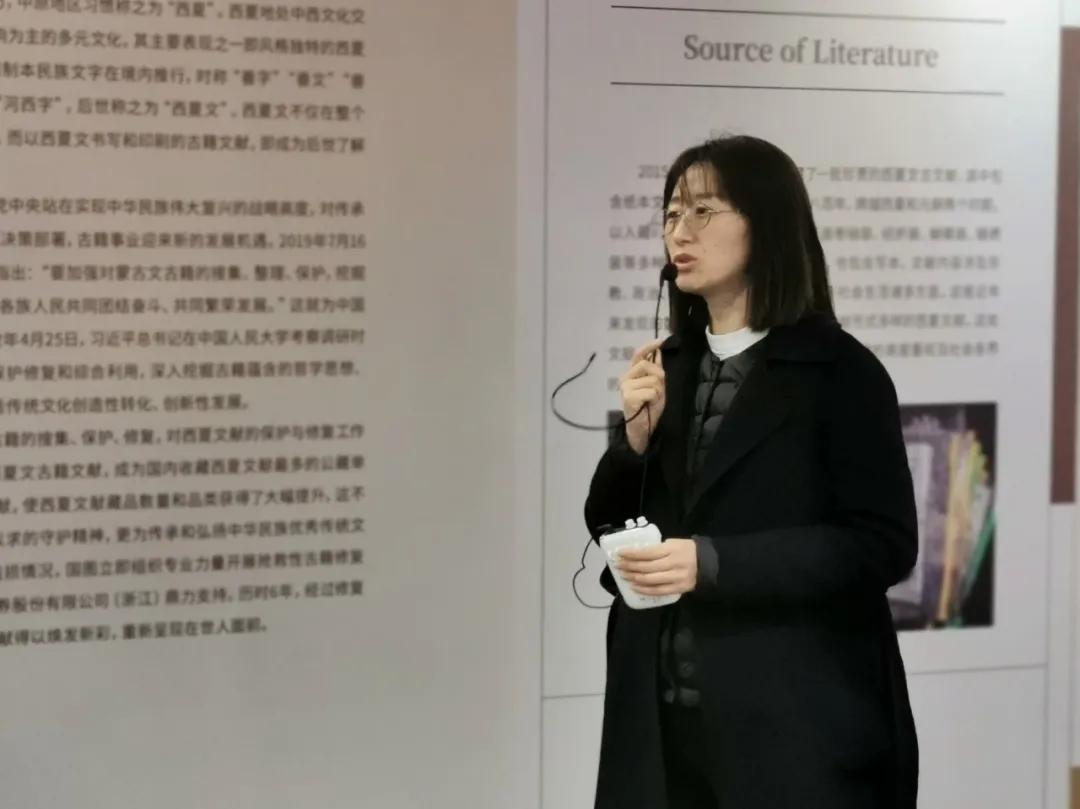
天津師范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青年教師胡艷杰
這些課,看似尋常,但來得珍貴。
老師是從不同地方被“挖”來的——胡艷杰曾在天津市圖書館歷史文獻部工作了17年,周余姣是中山大學、天津師范大學的雙博士后,還有來自北京大學、復旦大學、南京大學、浙江大學、南開大學等高校的博士,基本是“80后”和“90后”。
為使教學內容更豐富,古籍保護研究院開設了實操實訓的課程。天津師范大學圖書館特藏部古籍修復師牛甲芝,負責講授古籍的裝幀與裝裱。上課地點在校圖書館古籍修復室,學生站得滿滿當當,牛甲芝索性把案桌搬到無人的走廊上。
破損的書,需要細心拆除縫線,逐頁補齊,再捶平,重新裝訂。牛甲芝注意到,其間從沒有人說笑,學生們各自把著案桌一角,彎腰站著,認真操作著修復工序。看到完成得好的,她的笑意從口罩后流露出來。

天津師范大學圖書館特藏部古籍修復師牛甲芝
牛甲芝有常年戴口罩的習慣,除教學外,她還承擔著校圖書館日常的古籍修復工作,遇到破損嚴重的書冊,口罩得戴雙層,“絮化太嚴重了,像柳絮一樣,稍微一喘氣,紙渣就飛跑了”。牛甲芝今年38歲,因長期低頭工作,頸椎尤其不好,有時補了一天書頁,一抬頭,“瞬間覺得眼前一黑,天旋地轉的”。
手指摩挲過的文明向更遠處漫去。6年間,一批批畢業生接連步入各地博物館、研究院、紀念館,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古籍部、武漢大學圖書館古籍部、貴州民族大學圖書館特色資源中心等古籍保護一線崗位。
年輕的老師,年輕的學生,乃至更多的后來者,都在古籍中獲得綿長的滋養。
始乎博,終乎約
天津師范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的師生常提起一個名字——姚伯岳。
姚伯岳今年61歲了,但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,額頭寬闊,總是笑瞇瞇的。他步子很穩,走路也快,講話卻很慢,會指著路面上的銀杏果饒有興致地點評:“還是應該種雄樹,雌樹會一直落果。”說完自己不好意思地笑笑,“哎,我總是愛瞎操心”。

姚伯岳(左)為學生答疑
下午2點,日光明媚,天津師范大學圖書館12樓9號教室,20多個學生坐成一圈,上的是古籍鑒定與編目。
姚伯岳是該校古籍保護研究院常務副院長,他的課上不乏慕名來旁聽的人。大家知道,眼前這位老師,曾在北京大學與古籍打了大半輩子交道。
17歲那年,姚伯岳以內蒙古自治區文科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,讀研后,在北大圖書館進行專業編目實習。當時因條件受限,未編的古籍大多攤放在校內各個建筑的頂層,長久的雜亂無序,加之風吹日曬,輕輕拿起一頁,“土嘩啦啦地往下掉”。姚伯岳說,“心也跟著紙頁一起痛”。
破損、散亂的古籍,在姚伯岳腦海里揮之不去。22歲的年輕人暗自立誓,要做一名圖書館員,讓北大40萬冊未編書,能在書架上干凈、有序、安然地存放。
姚伯岳畢業后留校任教,講授《圖書館古籍編目》和《版本學》等課程。一有空,他就自己鉆進圖書館,給古籍進行編目。編目組的人見他是真喜歡,主動給他留了一張小桌、一把椅子,他掩不住雀躍:“用現在的話講,我也是有工位的人了!”
1998年,北大圖書館新館擴建完成,未編書的編目工作即將啟動,姚伯岳得知后,主動申請從教學崗調入教輔崗,告別講臺,任北大圖書館古籍部副主任和古籍編目總校。此后的20年里,他帶隊完成近40萬冊未編古籍的原始編目,發現了大量有價值的古籍品種和版本。
何為編目?散亂的古籍要一函函、一冊冊地配齊,破損嚴重的古籍要甄別修復。沒有函套的古籍要新做書套,版本要鑒別考證,古籍上的藏章印記要辨認著錄。要做主題和分類的標引,要給出典藏號中著者的四角號碼,書目記錄要掛接電子掃描的書影圖像。
古籍及其函套上有長年積攢的灰塵,也靠編目員吸塵去除,輕了,會除不干凈,重了,又怕損壞,對待古籍,像小心翼翼地捧著一個新生兒。有的館員因長時間手握吸塵器,大拇指都不會打彎了。
姚伯岳佩服捷克作家尤利烏斯·伏契克,“明知即將赴死,仍在獄中寫下《絞刑架下的報告》”。信仰足夠堅定時,內心也隨之富足和幸福,因而,姚伯岳總愛笑。
但學生們見過他流淚。
那是在一堂課上,姚伯岳回憶起在北大圖書館的時候,某天他突然發覺,身邊最年輕的館員,竟是1967年生人,很快,大家都會退休。而那時北大圖書館仍有近20萬冊未編書,如果不能盡快培養出新的接班人,不僅是北大圖書館,整個古籍事業將面臨斷代。一行淚不覺淌了下來,“我的前面有先輩可追隨,回頭一看,后面沒有人跟上,這是我最傷心的事”。
姚伯岳默默算著,當時全國僅復旦大學有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,高校里開設古籍編目課程的僅復旦大學、中山大學兩所,全國專職的古籍編目員不超過100人,而古籍數量超過5000萬冊件,培養一個合格的編目員至少需要5年……
雨中黃葉樹,燈下白頭人。
55歲這一年,姚伯岳告別了相伴38年的北大圖書館,來到天津師范大學。他要為古籍事業的后來者,點一盞燭燈。

學生在上古籍實訓課
繼以往,為將來
接勵見到姚伯岳,是在第二屆古籍保護學科建設研討會上。自成為天津師范大學圖書館黨委書記后,她馬不停蹄地采買古籍相關的設備,邀請專家來開講座。
2007年“中華古籍保護計劃”在全國啟動后,天津師范大學圖書館率先完成館內15萬冊古籍的普查與編目工作,其中10部入選《國家珍貴古籍名錄》。2014年,天津師范大學圖書館入選“國家古籍保護人才培訓基地”,2016年入選第五批“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”。
“高校的工作是育人。一所學校對文化的認知,決定了它的學生們對文化的認知。”中國古籍保護協會副會長鐘英華說道。他認為高校是實現文化可持續引領的重鎮,通過青年化、現代化的方式開展教育,培養具有豐富文化意涵的年輕人。
帶著天津師范大學成立古籍保護研究院的構想,接勵和校領導多番拜訪姚伯岳,請他出任研究院帶頭人。同為圖書館人,對古籍有共同的眷戀,也有著同樣的心之所向——非為以往,非為現在,而專為將來。
一個成熟的圖書館人如同“雜家”,需既懂知識,又懂技術。姚伯岳形容,“心里首先要有一座圖書館,才能清楚手中未知的古籍應放在什么位置”。
卷帙浩如煙海,從業人數卻寥寥。鑒定、編目、修復、數字化傳播,古籍保護的每一個環節都面臨無法與存量匹配的“人才荒”,遠遠趕不上古籍折損與老化的速度。
若進一步盤究,人才困境指向多方面的原因——傳統的“師帶徒”模式培養周期長,方法也不盡完善;全國高校逾3000所,其中開設古籍保護方向的不到40所;彼時全國尚未設立古籍保護專門的學科,古籍保護作為研究方向分散在中國歷史文獻學、古典文獻學、信息資源管理、文物與博物館、圖書情報學等專業下。
沒有專門學科的弊端在就業時開始顯現。上的是同樣的課,學的是同樣的內容,校招時才發現,用人單位不看方向只看學科。譬如有的單位急需古籍編目員,專業要求僅限圖書情報學,那么文物與博物館專業古籍保護方向的畢業生就無法應聘。學科不明確所導致的匹配失敗,加重了古籍事業的“人才荒”,學生滿腹委屈,用人單位也覺可惜。

學生在做古籍裝幀練習
2024年1月,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將“古籍保護與文獻學”作為二級學科,納入一級學科“信息資源管理學科”下。古籍保護不再只是一個研究方向,而作為學科被正式建立起來。
求索的腳步還在繼續。姚伯岳認為,文獻學是靜態的,可以給各個學科做輔助,但古籍工作是動態的,范圍也更宏闊,古籍保護不能停留在針對實體的原生性保護,而應實現從“藏”到“用”再到“活”的飛躍,需要數字技術與人文內涵的結合,需要再生與傳播。以上這些,都是文獻學無法全面覆蓋的。
古籍保護具備交叉學科的典型特征。自然科學領域的物理、化學、生物、材料、計算機等,人文科學領域的文學、歷史、哲學、地理等,管理學領域的圖書、情報、檔案、文物等,以及藝術學、非遺技藝等,這些都與古籍保護有關,但每一個學科,都不能完全涵蓋古籍保護的全部范疇。姚伯岳希望,古籍能仿照文物學科,成為交叉學科下的一級學科。
成為一級學科還需多久?接勵只知道,還有很長的路要走,而她明年就退休了。
古籍保護研究院成立以來,接勵幾乎全年無休,不斷考察調研,引進了一批青年人才,她懂青年教師的“痛點”,特意針對不同教學內容分領域引進。
“學科建設需要年輕人互相支持,咱別互相‘打架’,別幾個人都擠在一個領域里發論文做項目。”接勵說道。她用“請教”一詞來描述古籍保護與其他相關學科的關系,“像歷史文獻學、圖書情報學這些‘老牌學科’已經很成熟了,我們像牽著大人的手走路的小孩”。
“小孩想領著大人走,還得等慢慢長大。”
長不熄,無改時
2023年6月,習近平總書記考察中國國家版本館,走進保藏古籍版本的蘭臺洞庫,叮囑工作人員:“我最關心的就是中華文明歷經滄桑留下的最寶貴的東西。中華民族的一些典籍在歲月侵蝕中已經失去了不少,留下來的這些瑰寶一定要千方百計呵護好、珍惜好,把我們這個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繼續傳承下去。”
中華載籍,其所以得垂世久遠,端賴先人之善保護。長久以來,因兵燹水火使保存至今者不足百分之一,但歷代先人青燈黃卷,苦心孤詣,使典籍得以存續。
后之視今,亦猶今之視昔。
古籍版本學家、上海圖書館原館長顧廷龍曾言:“全國圖書館的古籍,沒有一家的家底是清的。”董桂存對此深有體會,他是天津師范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的青年教師,同時擔任古籍編目研習中心副主任。他坦言,外界得知天津師范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成立后,周邊的很多學校,乃至鄰區的公共圖書館,都會把古籍送來請他們幫忙。

學生對書頁進行修補
在海外,也存有一定的中國古籍,總數達數百萬冊。“古籍是孤寂的,只有我們去搶救,它才真正地活著。”古籍保護研究院青年教師凌一鳴,曾在2020年受邀前往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進行為期半年的學術訪問,參與該校所藏中文古籍的編目工作。他的想法很簡單,既然那里是海外中文古籍收藏的重鎮,就必須得來看一看。他希望通過中國人的努力,使世人知道,“這些古籍未亡,它們還存活在世”。
姚伯岳給每屆學生都講過一個故事:明末清初,常熟錢謙益的絳云樓收藏極為豐富,尤其珍秘孤本極多,堪稱當時天下私人藏書之首。藏書家曹溶曾想借閱某藏本進行謄錄,遭拒。誰知沒過多久,絳云樓不慎失火,萬數藏書盡焚。
“秘藏古籍百害無一利。”姚伯岳對此痛心疾首,只有以開放的情懷讓全社會利用古籍,才能做到真正的保護。他極力推動在校生成立了古籍保護學社和蒹葭讀書社,多年來,學生志愿者接力完成天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、文學院古籍的編目工作,還積極響應中國古籍保護協會的號召,利用寒暑假時間,走出校園,幫助各地其他圖書館。這正是老師們希望告訴學生的——古籍是攤開的手掌,不是攥緊的拳頭。
授課第6年,姚伯岳仍堅持著做新課件的習慣,為一堂課,他準備了97頁課件。講課全程站立,3個小時后,他才敢喝一口水。
課后,大家圍著他問道:“您覺得自己成功了嗎?”姚伯岳哈哈一笑:“我這輩子就做了一件事,這才哪到哪!”
又問起一年來最高興的事,姚伯岳不假思索地回答,是研究院的三位老師相繼都有了孩子。
他語氣飛揚:“雖然這些小寶寶長大后不一定從事古籍保護,但真的,給我一種感覺啊,大家的生活紅紅火火,我們的事業,人丁興旺。”
課畢已是入暮,學生們意猶未盡,跟著姚伯岳走出教學樓。這是一個珍貴的瞬間:姚伯岳放緩了步子,身旁是四個學生,夜闌人靜,頭頂的月是千年的月。
來源:2024年5月24日 中國青年雜志微信號